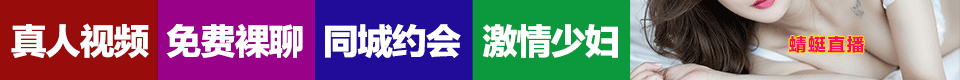高考结束了在家裏呆了几日,感觉很郁闷和压抑。
总想找个地躲躲,因为自己认为水准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可思前想后也没想出个能让我呆很久的地方。
在家躺了几日,一日我在市晚报的一个角角裏看到了一则招英语家教的资讯 。
我顺手拿起了电话打了过去。
在电话裏我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并着重提到了我在高三时在市里英语大 赛得了第二名的一些情况。
她表示了兴趣,告诉了我一个地址,同意明天见面谈谈。
第二天,在我出门时我好好的把自己修饰了一下。
心想第一次见人家要留个好印象。
搞的就像是去约会似的。
我按照她说的地址六点准时来到了北苑家园A座X室。
她的家是三室两厅,装修的很阔气,也很有格调。
我坐在沙发上,她给我到了一杯水。
那喝水的杯子很特别也很精緻。
象我这样的土人她可能一下就能看出来。
她又开始问我:「你先介绍以下你自己吧。」
「我们家裏我和我姐姐俩个孩子,姐姐已经嫁人了。我叫陶伟,高178, 体重150,今年参加的高考。」
「你不是大学生啊?」
「不是,但你请放心,我的英语水准很高的。」
我自信地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确信她多少有些嫌我小。
当我问她:「你的小孩在那裏呢?」
她笑了:「你看我象有小孩的人吗?」
「那谁补习英语呢?」
「是我呀!怎么很奇怪吗」?我是心裏感觉有些奇怪,可嘴上说:「没什么 。」
「其实我和你讲,我呢平时下班在家没什么事我想学学英语。以后可能用得 上。自毕业以后就没用到英语,所以英语书再也没翻过。」
「哦。」
「以后你每天七点钟到我这来,英语讲两小时,一小时复习,每天我付你1 00元,你看怎么样?」
我有些不能确定她说的钱数:「不用那么多钱的。」
她笑了:「你还真实在。就这么定了,我付你这个数,周结。你如果考上大 学也需要的。不过你可不能胡弄我啊。」
我连忙说:不会的,我一定会努力做的。
」
心裏有点感激她。
给她讲的英语都是些常用语,很简单,我也不费什么力气。
一周过去了,我给她上的英语课她感觉很好,我也很高兴。
在这一周裏我知道她结婚一年了,老公是搞土木工程的,在结婚一个月后就 去了孟家拉的工地了。
她的家在外地,毕业分配到市YY设计公司的。
本市也没什么特亲密的朋友,下班了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呆在家裏。
星期一我准时来到她的住处。
她开门时我发现她脸色不太好。
正当我要给她上课时她对我说:「姐今身体不太舒服,你就陪姐呆一会儿好 吗?钱我给放在桌上了你回头走是拿着。」
「姐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呢?」
「没事的,我躺一会儿就好。」
呆了许久,我看这她好难受的样子,就说服她去医院看看。
重感冒。
从医院回来,我把她扶到卧室的床上,给她倒了杯开水让她吃下药,扶她躺 下,我给她盖上了被子。
我对她说:「姐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
她突然拉着我的手说:「今晚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说话时我看到了她的眼泪。
说实话看到她落泪我的心也酸酸的,我拿纸巾一边给她擦着泪一边对她说: 「姐你别哭好吗,看你这样我也好难受,我留下来陪你还不行吗!」
她听到我这话就好多了。
可我有些后悔,我该和家裏人怎么说呢,我开始琢磨着。
后来想了想只有撒谎了。
我拿起电话先给我姐姐家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我今天晚上和几个小弟兄有事不回家了,家裏问起就说我在他家裏呢 。
姐姐还想继续问什么我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又拿起电话打给家裏说姐姐找我有事我今晚不回去了,直接去姐姐那 。
撒谎的人就是要不断地用一个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
和家裏一切都说妥以后,我坐在媛姐的床边上。
她眯着眼睛。
我那时真的不知道该和她说点什么。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当她一睁眼的时候,我赶紧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但还是被她看见了。
「你看姐姐半天了,姐姐好看吗?」
「好看,好看。」
「嘴够甜的。」
「不是的姐姐。你就是长得好看。」
我那时真的有些愚和傻,可能也正是这些使她觉得我比较老实忠厚。
就在我不知在这时刻该和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床头放着一本《百年孤 独》,我拿起了那本书说:「姐姐我给你读书听吧。」
她没有拒绝,我就从插着书签的那页给她读了起来……那一夜我是在趴在她 的床边度过的……回到家快中午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没有上班。
他见我回来了就把我叫到了跟前。
突然他拽着我的耳朵严厉地说道:「说,你昨天晚上去那裏了?」
「我去姐姐家了。」
父亲的手加大了力度,「你敢撒谎。」
我看没办法了,就说:「我和我们那帮同学玩牌去了。在冬冬家。」
父亲松开了手,接着给了我一个嘴巴,「以后你敢再撒谎看我怎么收拾你。 」
说完「哐当」
关上门走了。
我高兴的心情瞬间变得郁闷起来,心裏在怨恨姐姐为什么不替我保守机密。
傍晚母亲下班和姐姐一起回来的。
一进门母亲就问我,「你昨晚跑那裏去了?你爸爸昨晚临睡时给你姐打了个 电话让你接电话,你姐说你不在,是去冬冬家玩去了,可你爸不放心。为你担心 了一晚上。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呢?」
我没有辩解什么。
可能是母亲看到了让我一下午都感觉火辣辣的那半脸还红着,就问道:「你 爸是不是打你来着?」
我只是点了点头。
母亲让姐姐给我那来一条热毛巾敷在还红着的那半脸上。
晚上,我那裏也没去,吃过饭就跺进自己的房间裏,心裏老是惦记着媛姐不 知道她怎么样了。
那一夜我梦见了她……是第三天的上午,媛姐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怎么不管我了。」
「不是的媛姐,这几天家裏发生了点事情。」
「哦,那今晚来吗?」
「来。」
「那你六点钟来吧,到我家裏吃饭。」
「好的。」
晚上,在媛姐一开门的剎那,我楞住了,她穿着一件很薄很薄的睡衣,我朦 胧地看到她那大大的乳房。
「傻看什么,一会姐姐让你看个够,来,快进来。」
我随她走进餐厅,只见桌上摆了六个菜,还放着一瓶红酒。
「来,为了感谢你那晚对我的照顾,我们干一杯。」
「媛姐,我不会喝酒。」
「没事的,少喝点。」
说着她一仰脖满满的一杯红酒干了,她拿着空酒杯对着我说:「给姐姐个面 子好不?」
我心想我这一杯下去我肯定完了,但我不能老这么僵着,我心裏喜欢她,为 了她高兴我豁出去了。
我拿起了酒杯一饮而进。
「还说不会喝呢!」
「姐,别倒了。」
「我先倒上,下来我们慢慢喝。」
我们在音乐飘荡的屋子裏继续喝着……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嗓子眼在冒火。
不知为什么我变得兴奋起来。
「来,姐,我敬你一个。」
说完我一口就干了。
「要不你别喝了。」
「不,我要喝。」我推开她的手的时候我的手却不知怎么停在了她的胸前。
我虽喝的有些多,头脑也有些发热,可心裏多少还明白些。
我急忙想把手挪开,可她的手却紧紧的把我的手按在那,我的身上越来越热 ,心砰砰的直跳,我的下面象控制不住的似的变的越来越大。
「想姐吗?」
「想。」
「那姐让你看看怎么样?」
我点点头。
当她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种饥渴和害羞的感觉,说实话她是我 第一次看见一个完整裸体的女人。
她脱去我身上的衣服,我心跳的更厉害了,而当我们亲吻起来以后,感觉一 切都不存在了。
起初我和她亲嘴还是闭着嘴的,后来她让我张开嘴,她把舌头放在我的嘴裏 ,我的整个身体在发颤,在发抖……一股股热浪从身上涌到头上。
慢慢地当我的舌尖和她的舌尖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涌上心 头。
后来她让我插进去,可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做,她把我的弟弟放在她的私处, 对我说:「你慢慢地往裏插。」
我感觉我下面硬硬的东西顺着粘粘的液体插了进去,裏面热乎乎的。
「你抽出来再插进去。」
我上下没动俩下就觉得身体裏有一股液体控制不住地奔了出去。
「我——」
「没什么,你累了,歇会一会儿再来。」
也不知歇了多久,我们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当第二次感觉液体奔出去的时候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我趴在她的身上仍不想马上下来,我感觉她的下面一动一动的,每动一下都 揪着我的心。
「姐姐好吗?」
「好。」
「以后会忘了姐姐吗?」
「不会。」
「以后想姐姐了就来找姐姐。」
「嗯。」
那一夜我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睡着的。
醒来时我和她都赤裸裸的躺在床上。
我这时候有些害怕了,我坐了起来,这时她突然从后面楼住了我,她的舌尖 在我的耳朵边游离,我心裏痒痒的,我变的不安起来,我一下子把她从后面拽到 我的前面,我们的舌尖又缠绵在了一起……我再次和男孩身做了告别。
离开媛姐家又快到中午了,我这才感觉到完了,又一晚没回家,肯定又要挨 揍了。
一想起来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我跑到了冬冬家找到冬冬,让他陪我一起回家算是帮我证实一下。
我心裏又盘算着谎话怎么说。
一进屋,父母都在家,我心想坏了,爸爸和妈妈看见冬冬来了,对他还算客 气。
冬冬和爸爸解释说:「叔叔,伟哥昨晚在我们家睡的。他昨在我们家喝多了 点,他怕你打他没敢回来。」
爸爸没有理他,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就转向我母亲说:「阿姨,我先回去 了。」
说完几乎是跑出我们家的。
这时候爸爸拿起一跟南傍国朝我抡过来,我没有躲闪,这一棒打的我脑袋开了 花,整个人顿时坐在地上,整个脸血乎乎的。
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吓坏了,嘴裏直喊:「儿子,儿子。」
爸爸瞬间也傻了眼,可能他感觉到我会躲闪的,可我偏偏站在那裏没动。
只听母亲对父亲吼道:「你还楞着干什么,还不赶紧送医院。」
后来怎么进的医院我都不记得了,醒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脑袋上缠 着绷带。
母亲陪在我的身边。
她看到我醒了。
苦涩地对我说:「孩子你可醒了,你知道妈有多担心吗?」
我的眼裏浸满泪水。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真的很难熬,每当我一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和媛姐的那个 晚上,心裏也非常渴望那样的晚上再现。
一天的晚上爸爸和妈妈还有姐姐走后,我一个在病房的走廊裏走来走去的, 心裏就象猫抓似的,心神不安……不行!我要见她,我心裏真的很想媛姐。
我熘出了病房,搭了个车到了媛姐的家。
她开门时看到我的样子吓坏了。
当和她全盘托出的时候,她心疼地把搂在怀裏,嘴说:「都是姐姐不好。」
「不怪你的,姐姐。」
「姐姐我可想你了。」
「我也想你。」
我们又缠绵在了一起。
她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
我回到病房时又遭到了值班护士的怒斥:「你跑到那裏去了?谁允许你出去 了?出了事谁负责?」
「你啰嗦什么,我不是回来了吗!」
我转身要走时,只听她在背后说了一句:「没素质。」
我真想和她大闹一场可又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就装着没听见,回了病房。
原本快乐的心情此刻已降到了低谷。
拆缐是姐姐陪我去的,拆完缐医生没什么大碍了。
我和姐姐说我要出院回家。
她和我说等妈妈下午来了再说。
下午我看到妈妈一进病房她特别高兴的样子,就问她:「妈什么事让你这么 高兴呀?」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说着她从口袋裏掏出了一封信。
我接过来一看,是S市建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也高兴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我的快乐就消失了,我一想到去S市要离开媛姐我就高兴不起 来了。
在我要离开家去S市的那天上午,我跑到了媛姐的家裏。
她请假在家。
我们不断地亲吻着,我吻遍了她的全身。
我们不停地做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我们都浑身软软的……她送我出门的时候,紧紧地把我拽到怀裏,在我 耳边说:「答应我,在大学裏不许交女朋友。」
「媛姐,放心,不会的,我心裏只有你。我不会再爱另外任何一个女孩的。 」
她哭了:「想我就回来看我。」
「嗯。」……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疯了,就听爸爸吼道:「都这个 时候了你又野到那裏去了?」
姐姐忙插嘴说:「快点吧,再不走就赶不上了。」
在计程车上妈妈不停地和我说:「以后一个人在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吃东西要注意卫生……」
她几乎是说了一路。
在我上火车的瞬间妈妈又把我拽住了,在我耳边低低的说:「儿子,妈给你 在白云贯算了一卦,说你命裏犯桃花运,你以后自己在外离女人远点知道吗?」
「知道了妈,你放心吧,我大学裏绝不交女朋友。」
「那妈就放心了,上车吧。」
当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媛姐,我的手不停地朝远 处挥动着……一直到火车消失在远方。
当我停下舞动的手,心裏有些酸酸的,那时我真想跑回去对媛姐说:「我不 能没有你!」……我进入大学的生活还算顺利,没多久我很快就适应校园的生活 。
可三个月后一天我特想媛姐,心裏就象有个蠕动虫子很是受折磨。
我拿定了主意,我要回家。
当我站在媛姐家门口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敲着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
她疑惑地看着我,象看贼似的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很粗俗地说:「你找谁 ?」
「我找媛姐。」
「出国了,房子的主人现在是我。」
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可能我刚才的敲门声吓到她了。
我急忙赶到电话厅给媛姐的公司打了电话。
当我确信我朝思梦想的媛姐真的出国了,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在街头流浪着,我也不敢回家。
那一夜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当我踏上回校的列车的时候,没了家裏人 的送行,没了媛姐,可我还是举起了右手,仍向远处挥舞着,我在告别,向昨天……